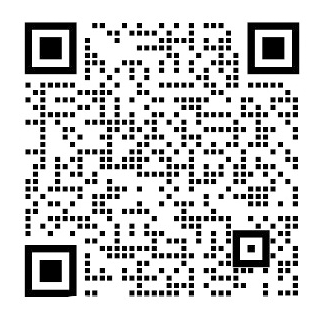景承的回答让我震惊,几天前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疯子说的话,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偏偏并没有质疑眼中这个男人给出的答案。
某一刻他的确像是怪物猎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精明和睿智,而是他更像一个专门猎食物同类的怪物。
“如果凯撒已经被你抓获,那在这里行凶的又是谁?”我诧异看着镜中景承的脸。
“我是被你从精神病院带出来的疯子。”景承最后整理好衣服,转身摊摊手。“不是百科全书,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知道答案。”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我多少有些失望,原来他并非无所不能的存在。
“想知道答案?”
我点点头。
他把短款的风衣递给我,示意我换下身上的警察制服:“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景承开车去了城外的郊区,坐在一辆疯子开的车上,我唯一还能做的只有检查安全带,试图从广播中得知关于这个案件的进展,换了几个频道,从车载音响中传出一首曲调悲伤的歌。
是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词曲都透着浓浓的无奈和哀伤,我正想调换时景承拨开我的手,我这才发现影响中那个反复无常的疯子不见了,落寞的忧郁写在他脸上,看着车窗前方的双眼透着追忆的眷恋。
这个眼神我不是第一次看见,他带我去燕栖大厦坐在露台他给那杯没人的茶杯倒茶时,也是这样的表情。
他突然变的沉静,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靠在车窗放在嘴边,车里弥漫着歌曲的悲伤,他沉醉于歌声之中任凭长发在风中飘舞,他似乎被这首歌所触动,原来他是有情绪的,我看见了他的孤寂或许那才是真实的景承。
一路上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歌曲结束后车里陷入漫长的沉寂,难得看见他如此的安静,虽然认识他才两天时间,我竟然有一种把他当朋友的错觉。
三个小时后车停了下来,走下车我看见一处面积很大的建筑,被高大的墙体牢牢围住,密布在上面电网和哨楼上荷枪实弹巡逻的军警让人感觉到紧张和压抑。
这是城北监狱。
全省设防和守备最森严的重刑犯监狱,里面关押的都是穷凶极恶十恶不赦的罪犯,其中一半不会再从里面走出来,我还是学警的时候警校组织参观过这座监狱。
“走,带你认认路,要是你输了这场游戏,这里就是你最后的归宿。”景承欢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他又恢复了疯子的本性,之前那个忧伤敏感的男人已经荡然无存。
我无语的白了他一眼,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上一次来这里,我还是警察,我用威严和正义的目光去审视那些被关押的罪犯,而如今有一种自投罗网的感觉,不曾想到有朝一日我会以在逃凶犯的身份重回这里。
我很了解这里的设防等级和进出流程,别说一个疯子和一个在逃凶犯,即便是来这里公干的人员也会经过层层核查,绝对不是一本警官证就能蒙混过关的。
他都还没告诉来这里的原因,我刚想提醒但他已经站到值班警卫的面前,我看他对警卫说了几句什么,警卫转身打了一个电话后向景承走去时我手心全都是冷汗。
哨楼上巡逻的军警居高临下看着我们,这个距离只要我们有异动,可以在不请示的情况下射杀。
咔!
监狱的侧门被打开,警卫示意我们可以进去,我半天没有回过神,很想知道景承到底说了什么,就凭几句话可以开启重刑犯监狱的大门。
我埋着头心虚的跟在景承身后,跨过侧门后听见身后沉重的关门声,怯生生向后望了一眼,厚厚的铁门阻挡了视线,连同一起被阻隔的还有自由和希望。
没走多久前面有一名穿制服的狱警,警衔是三星两杠的一级警督,估计在城北监狱的职务不低,他居然是在等我们,也没有多余的话,只面色严肃对景承点了点头看上去他们应该认识。
我越来越好奇景承的身份,一个可以接触到警方绝密档案,一个可以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自由出入重刑犯监狱,一个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跟着警督走向城北监狱的深处,看见一栋被电网隔离的低矮楼房,外墙被刷成刺眼的白色,和城北监狱的其他监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这里对于关押在城北监狱中的犯人来说,却是一个忌讳莫深的地方。
我记得这栋被电网隔离的楼房还有一个名字,黑楼。
这是死刑犯监室,也是执行死刑的地方。
黑楼里面的守卫更加森严,通往黑楼内部的道路并不长但被十多道铁门分割,每进一道都由警督签字通过,最后停在一处门口站有警卫的监室门口。
“一个月后执行死刑,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从见到警督到现在,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警督离开的时候把钥匙交给他,也叫走了门口的警卫,剩下我和景承站在死寂般的长廊中,景承久久矗立在监室的门口不动,我竟然发现他在犹豫,甚至还有一丝不安。
我第一次发现还有可以让他心绪不宁的事存在,开启监室大门的钥匙就在他手中,景承已经搓揉了很久,忽然明白让景承踌躇不前的并不是这道大门,而是监室中关押的人。
我很好奇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让一个反社会人格的疯子顾虑。
“进去后尽量埋着头,不要和里面的人有过多的视线接触,更不要说话。”景承低声对我说。
“哦。”
他回头看我,目光充满了认真和严肃。
“知道了。”我重新回答。
景承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坚定的打开监室,或许是被景承提醒,我跟在他身后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惨白的灯光让监室显得格外冰冷,厚厚的玻璃隔断把监室一分为二。
景承坐到隔断边的椅子上,中间的台面上是一副摆放整齐的国际象棋,只能容下两只手的门洞是隔断两边唯一的连接。
我按照景承的叮嘱尽量把头低埋,但还是好奇想知道让景承都会有所忌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隔着玻璃我看见一个穿着蓝白狱服的中年人,年纪大约四五十岁,头发梳理的一丝不乱,鼻梁上的眼镜让这个人看上去温文儒雅,手里拿着一本书,我抬头的时候刚巧他合上书页,我看见封面的书名。
权力意志。
巧合的是,在我第一次见到景承的时候,他看的正好是同一本书。
那人动作沉稳优雅把合上的书放在旁边,在他身上我竟然看到几分景承的影子,特别是他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时,那笑意洒脱磊落典雅,像极了景承经常挂在嘴角的微笑。
中年人从容的坐到景承对面,但却没有去看我和景承,目光专注的看在他和景承中间的棋盘上,双手相对呈三角形放在嘴唇边思索,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是神情都流露着自信和平静,和我旁边的景承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的自负、狂妄和骄傲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只看见一个拘谨、如临大敌的景承,从进到这间监室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他的微笑,取而代之是全神贯注的戒备,我始终不明白玻璃对面这个中年人为什么会让景承如此小心翼翼。
监室并没有因为多了我和景承而打破沉寂,安静的让人感觉到窒息,中年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持白棋先行,景承不假思索的移动棋子。
我对国际象棋涉猎不深,但景承和中年人每下一步都没有半点的停顿和思索,在方寸的棋盘中不断有棋子被移出,棋盘上双方的棋子所剩无几,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厮杀的异常惨烈。
直至景承孤军深入,最后手持黑棋主教轻轻推倒中年人的王棋,面无表情声音低沉。
“你输了。”
课题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优先添加企业微信。